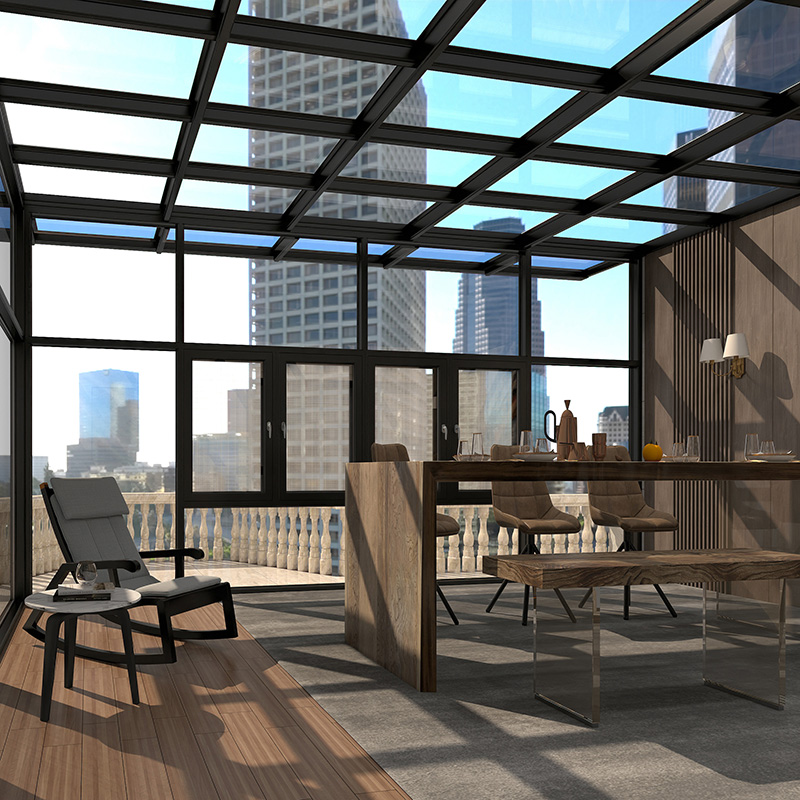《大家》2021年第4期|曹军庆:皮匠街的舅舅(节选)
发表时间: 2024-04-29 12:12:11 文章出处:云开全站app官方网站
曹军庆,中国作协会员,湖北省作协文学院专业作家。出版有长篇小说《魔气》《影子大厦》,中短篇小说集《雨水》《越狱》《24小说》《向影子射击》《会见日》等。发表文学作品三百余万字,曾获十月文学奖。
向忠良有一段时间混得还不错,就是给舅舅钱那一段时间,他开始打扮,买衬衣买西装买皮鞋。当向忠良穿上西装站在镜子面前,细细打量,他和舅舅同时发现,他还是个很帅的男人。他笑了,舅舅也笑了,他的笑容有点腼腆,仿佛经不起推敲。但确实笑了,他们为此感到踏实。
到了这样一个时间段,黄汉民仍然不知道他在外面干什么。县里穿西装的男人无外乎这么几类人:做生意比较成功的商人,开重要会议要求着正装的领导干部,有了自己地盘的黑帮头目和自以为功成名就了的文化人。那么,他是哪类人?向忠良非常容易归到哪个类别去呢?黄汉民不敢想,既不敢想,就不去想。向忠良还是天天外出,和从前不同的是他现在经常拎着包,拎着一只高档的黑色皮包。不知道那包里装着什么,反正鼓鼓的。虽然黄汉民不知道他在外面做什么,但只要回到家里,向忠良就特别安静,还很勤快,他无师自通地做着舅妈在世时做着的那些事儿,擦拭桌椅,清扫地面,重新装上瓜子,烧水倒茶。
做完这些,他就坐在角落里,看舅舅给人理发,听闲人们扯闲话。黄汉民明显老了,他在别人脑袋上摸来摸去的时间更长,动作速率也更慢。好在人家都不嫌弃他,他的呼吸也有问题,有时不得不停下来,要喘上好一阵子再接着干活。
每到这样一个时间段,向忠良心疼舅舅,却不表露,他也就把头扭到一边。黄汉民知道他在心疼自己,心里便多了份安慰。他在死的时候,跟向忠良说了很多话。
他说,“你舅妈六十三岁去世,我活到七十六岁,我比她多活了十三年,你知道她是怎么死的吗?”
“她是自杀的”,黄汉民说,“她清楚自己,知道没办法,她没办法我也没办法,她都知道,就走了这条路。她不想受折磨,不愿拖累我,她一生都不想给别人添麻烦,不愿拖累任何人,哪怕是我。”
“我是怎么知道的?也是事后才知道,事前不知道,她服药时加入了毒药。我愧对你舅妈,也敬佩她。她死得干净,死得清爽,没有经受痛苦,她为自己这一生的病痛画上了句号。”
舅舅没听到向忠良所说的话,也可能听到了,他的手渐渐冰凉,向忠良握着他,眼眶里有泪珠滑落。
剃头匠铺子关闭了好几天,老顾客们习惯性过来,推推门,敲敲门,再转身走掉,摇着头,失魂落魄似的,像是这才明白,黄师傅已经不在了。都是过去的老伙计,失去了老在一起聚的地方,顿时都有了失落感。
某一天,向忠良打开门,不声不响地操持起舅舅的旧业。第一个坐上理发椅子的人是老佟,老佟那天见剃头匠的门开着,欣喜地跑过来,站在门边探头探脑。向忠良满脸堆笑,拿着白布围裙,热情地招手让他进来。老佟一坐上椅子,竟有些百感交集。一样的味道,一样的气息,一样的动作。跟过去没什么改变,温暖的毛巾,剃刀刮过皮肤和毛发,发出轻微的滋滋的响声。
没想到向师傅居然什么都会,他应该没学过,黄师傅也没教过他。这屋子里的人都能作证,他和舅舅不能算是师徒。可是他都会,每一道手脚都很到位。他就是看得多,坐在一边看着舅舅一招一式做,看的时候都默记在心里了,一上手,已是熟门熟路。如此说来,舅舅还是他师父,他也是舅舅的徒弟。
剃头匠铺子接着开,向忠良好像是个天生的剃头匠,天生要吃这碗饭。来理发和来闲聊的,差不多还是那些人,其他都没变,变化的是师傅,黄师傅变成了向师傅。向师傅就是脚不方便,只有一条腿,要拄拐杖,好在不必走太多路,活动范围不大。除了舀水时,要走几步路外,其他时间都围着理发椅子转。向忠良不是先天瘸子,只是十年前他是自己从马坊街跑到皮匠街来的,当然,他是后来成了瘸子的。
墙上的电视机总开着,为大家闲聊时事提供佐证。向忠良跟舅舅一样,从不插话,以前还有人问黄汉民,你怎么看?现在没人问他。向忠良脸上挂着温厚的笑,有时难免苍凉,有时也有些恍惚。好像站在这儿理发的男人不是他,而是另一个人。他的身体站在这儿理发,魂魄却已到了别处,但也不影响他的动作,到底比舅舅年轻,手艺一点也不差。
都喜欢他,又干净,又不吸烟,就没有恶习。只可惜少了一条腿,可是他的腿怎么就少了呢?腿的秘密到底是什么?
向忠良继承旧业两年后,也就是舅舅黄汉民过世两年后,街对面的锦绣花园建成了。如今的皮匠街成了这个样子,一街两半边,半边旧半边新。对面裙楼里的门面房,纷纷开起小店子,巧合的是剃头匠正对着的那间门面,也开了间理发铺,叫早春发屋。
开业前一天,理发师林霞过来拜码头,她买了些鲜水果和糖块,过来分发。她穿着花裙子,洒了香水,长得漂亮洋气,开口说话却是我们本地口音。
在这儿理发的都是老者,年纪大的人,他们是这个社会里的遗老。不知为什么,他们莫名其妙地对她的漂亮很生气,反感她把店开在剃头匠对面,这不是明摆着要和向忠良摆擂台吗?理发铺哪里不能开啊,你偏开在这里。他们把塞到手里的水果糖块扔到地上,拿脚踩踏,要给她下马威。林霞嘴上的笑容僵住了,但是她说,“开在一块也有开在一块的好处,不是还有小吃一条街吗,大城市不是也有美发一条街吗,理发铺挨着理发铺,说不定人气更旺呢。”
这时,向忠良俯下身去捡糖块,捡没有被踩烂的水果。他单腿撑着,弯下身子很吃力,一只手还要牢牢抓着椅背。
林霞见状,也忙弯腰去捡,这一来,反倒弄得那些扔的人不好意思。林霞经营的是新式理发,除了理发,还有洗发、烫发、染发。但是不刮胡子,不剪鼻毛,也不掏耳垢,她和剃头匠的区别就在这里。
皮匠街的老住户不少,锦绣花园又住进了更多人。人增多了,人流量也变大了,林霞长得好看,找她理发的人自然就多。得排队,也有人看一眼先走了,等一会再过来。没走的人坐在店里说话,裙楼空间高,屋顶用木板搭建了阁楼,林霞晚上就睡在阁楼上。一楼是店子,放眼看去,坐在店子里等着理发的多是年轻男人。
林霞可能意识到了什么,不想惹麻烦,她大声跟人说话,有事没事总说,“是的,我结婚了,我老公在深圳呢,是酒店里的大厨。”
她还把跟老公的合影挂在墙上,就在镜子上方。果然是个帅气小伙子,不肥胖,并非每个大厨都肥胖,照片里,林霞甜蜜地倚靠在他肩头。
林霞此举,是做个告示,对大家说她有老公,还和老公很相爱。男人别打她主意,打也没用。可还是发生了多起纠纷,有个小伙子向另一个小伙子发难,怪罪他故意把烟喷到自己脖子上。“你抽烟就抽烟,往我脖子上喷什么,挑衅?”
另一个小伙子回嘴说,“你是个啥东西心里真没点数?前几天才过来剪过头发,现在又跑来剪,剪脑袋吗?”
说着,两人就在店里干了一架,之后又有另几起打架事件,起因全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。若在另外的地方,肯定打不起来,在林霞这里,偏偏就打了。还是有说不清道不明的争风吃醋,内心压抑着失望沮丧,随便一句言语不合,小伙子们便要动手。每次他们打架,向忠良都站在自己的屋子里冷静观望,神情平淡。
打架摔坏了洗发水,损坏灯箱广告,林霞哭笑不得。处理纠纷先是物业公司出面,物业不想报警,毕竟都是附近熟人,又不能不处理,就报告了皮匠街街道办事处。街道办事处分管治安的副主任朱正宽接到电话过来了,他也是第一次见到林霞,心里头扑通了一下,这一声扑通,他自己听到了,站在自家屋中间的向忠良也听到了。
此事严格说来没什么新意,天荒地老,不过如此,向忠良因此时常想念舅舅,和黄汉民在一起生活的十年间,倒是发生了更多不同寻常的事情。他感激舅舅,感激舅舅从不追问他荒唐的人生。哪个少年不荒唐,不过是代价不同罢了。可是舅舅给了他空间,给他自由,好也罢,邪恶也罢,都随他去。有一年他突然离家,一共离开了五个月,就是他穿上西装拎着黑皮包出门。那几年之后的某一年,他有五个月没有回来。舅舅坚持没打听,向忠良至今想起这件事仍然会哽咽,不能让舅舅知道那些细节。事实上舅舅也就是等着,他等着,不管什么事总能等到一个结果。
结果是向忠良回来了,回来的时候却只有一条腿,他是拄着拐杖回来的。伤口大概已经痊愈了,一瘸一拐地走着。没人知道他在这五个月发生了什么,到底在哪里丢掉了这条腿。他手术后,伤口愈合了才回来,最惨烈的时候他在哪里?此时他昂着头,像是专门在等着舅舅骂他,或是把他赶走。他脸清瘦了一些,看着好像更坚毅,脖子也更修长了一些,黄汉民并不觉得古怪,就像事情就该这样。即便如此,向忠良记得舅舅也没问他出了什么事,他们像一对父子,更像一对密友那样默契,那样心照不宣,就像是小心翼翼地不去揭穿他们共同保守的某个秘密,但黄汉民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,他默不作声地接住了他。
向忠良当天喝了两瓶白酒,咕嘟嘟地灌下去,然后,他又焚烧了那两套换着穿的还是八成新的西装后,便倒在床上昏睡了七天。
他怎么就不能安分一点?只不过现在他是拄着拐杖往外跑,不再穿西装,也不再拎着黑色皮包。林霞是个勤劳女子,晚上睡得晚,十一点之后才能收拾完毕,再上床。
老街狭窄,剃头匠跟早春发屋铺面相距也就五米,林霞在阁楼上开了扇小窗户,方便通风透气。夜深人静时,向忠良能听到她细小的声音,关掉灯,林霞也能清楚地俯瞰街道这边。她隐在窗户一侧,躬着身,能看到向忠良黑夜里的影子和动静。
- 上一个: 浙江日报 数字报纸
- 上一个: 【48812】肆无忌惮的权钱“旋转门”
- 我国风拱门门框
- 花编制的拱门PNG图片素材下载_拱门PNG_熊猫工作
- 【图】讨教高手怎样一张皮搞定POLO门板弧形包皮傍边不必缝线_PoloPolo Plus论坛_爱卡轿车
- 葛洲坝集团完结景洪水电站弧形作业门装置